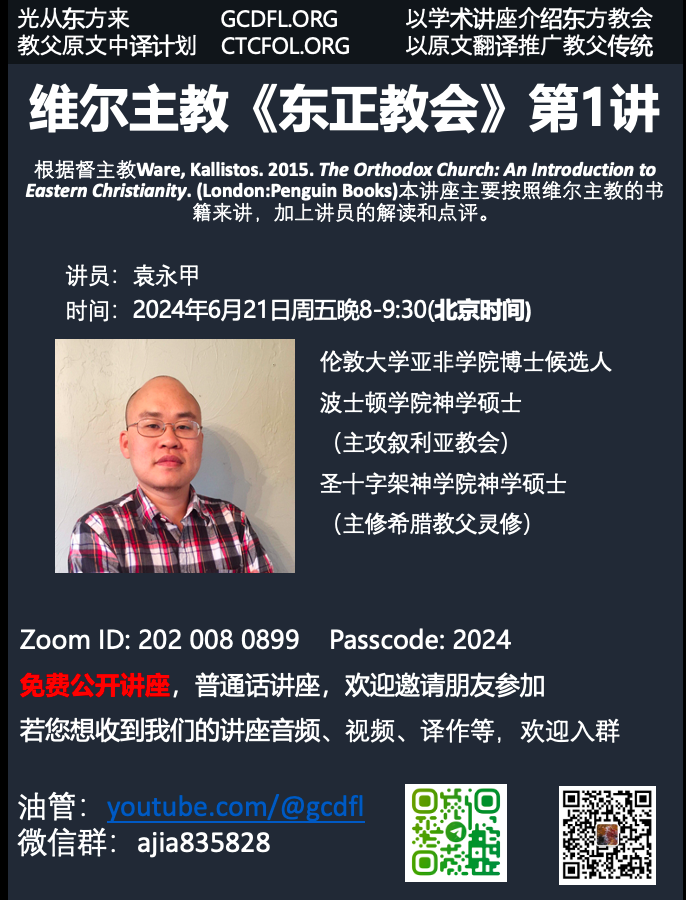-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课系列,第一章。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二课》,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4年6月21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和网盘下载,请见主页
-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此篇以体现维尔主教著作为主,若要听阿甲的评论,请听讲座。
正文
第一章 初始
‘村里有一个深挖于地下的小教堂,入口处经过精心的伪装。当一位秘密的神父到村庄访问时,他在这里主持圣餐礼和其他礼拜活动。如果村民们相信自己是安全的,没有被警察监视,所有人会聚集在教堂,只有守卫守在外面,在陌生人出现时发出警报。在其他时候轮流做礼拜。。。。。。
复活节礼拜在一个官方国家机构的房间内举行。只有拥有一张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入,我和我的女儿都有通行证。到场者约有三十人,其中一些还是我的熟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年长的神父主持仪式。我们轻柔欢快地歌唱着"耶稣升天了!"……参加地下墓穴圣堂的礼拜活动,让我感到很快乐,这份快乐甚至在今天给了我活下去的动力。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对俄罗斯正教会的信仰生活的两段描述。1
* 1选取于期刊《正教生活》1959,第四期 页30-31
但是如果对它们做少许改动,就可以用来描述尼禄(Nero)和戴克里先(Diocletian)统治时代的基督教崇拜活动。
阿甲按:拜占庭的政教关系为什么不是现代社会的政教分治?
在拜占庭帝国,政权是东正教的赞助者,但现在的西方不是这种模式。现在的西方是政教分离,现在有一些学者推荐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政教分治,即政治和宗教应该分开治理。但在君士坦丁时期及拜占庭帝国时期,并不能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彻底的政教分治关系。所谓政教分治,是指宗教可以自由发展,但政治不应干预。比如在美国,有东正教徒、新教徒和摩门教徒。还有耶和华见证人和东方闪电等。所有被传统教会归类为基督教异端的宗教都可以在美国自由发展,政治是完全不参与其中的。但在拜占庭时期并非如此,当时他们需要召开大公会议来确定哪些教义是正统的,哪些是异端。 然后将持有异端教导的主教和神父流放,解散他们的教会,并要求他们加入正统教会。因此,你可以看到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教会避免进一步分裂或产生更多的异端教导,起到了辅助作用。我认为无法用政教分离的概念来描述拜占庭时期的东正教与罗马帝国的关系。
阿甲按:哪个国家对宗教管控最严?
从我学习到的关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情况来看,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像君士坦丁这样的人物。中国历代帝王里面,没有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公开发布通告说基督教可以自由地崇拜和发展。最早的追溯到唐朝时,可以说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年代,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仔细了解当时的宗教政策,那基本上是唐朝只是容许他存在,并且管理非常严格。严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新注册的神父或修士必须登记在册。他们把登记的方式叫做“僧籍”,即从人口登记制度延伸而来的,是宗教的一些神职人员登记的一种政策。所以,在唐朝的基督教受到了政府严格的控制。当然它允许你发展,并且一度也很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景教碑上提到的“寺满百城”,很多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景教教堂怎么可能发展到每个城市都有。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留下的遗迹太少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基督新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它直到18、19世纪才开始传播,至今也不过两百多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可以几乎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多数城镇中都有基督教堂。因此,每个城市都有景教教堂并非一种夸张的说法。只是因为在历史长河中,景教的遗存由于长期受到政治的排挤,可能很多遗迹和资料都被销毁或取代了。这就是情况。我之所以提到这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希望寄托于人身上,不要抱有幻想,因为根据我所了解的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神亲自干预。我们必须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任何政治人物或领袖身上。我们当把希望寄托于主的大使命和应许,并且努力践行就足够了。
它们显示出基督教的历史在十九个世纪的进程中绕了一整圈。今天的基督徒比他们的祖父母辈距离早期教会更近。基督教起初作为微小的少数派的宗教,存在于一个非基督教势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这种情况现在再次形成。初期的教会是同国家相区别和分离的;现在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中,教会和国家之间的传统联盟走向了终结。基督教起初是一个「非法宗教 religio illicita」,受政府禁止和迫害的宗教;在今天,迫害不再只是过去的事实,它绝非不可能,由1918年至1948年的三十年中,为信仰而死亡的基督徒人数,超过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三百年。
情形使得正教会的成员尤其意识到这些事实,因为直到最近,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一个反基督教的共产主义政府统治下生活。从五旬节到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个阶段的历史,对现今的正教特别具有适切性。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一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徒2:2-4》
因此随着圣神在五旬节——第一个"圣神降临主日"降临于耶路撒冷的宗徒们身上,基督教会的历史开始了。在同一天,经过圣裴特诺宗徒的宣道,三千男女领受洗礼,第一个基督教团体在耶路撒冷形成了。
阿甲按:当信靠主的大使命
我自己对中国教会的情况并不乐观。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中国教会也可能面临着再一次的被政府彻底排斥掉的风险,就像当年的景教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点也不乐观。但是,在主耶稣的大使命方面,我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我的导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开过一次讲座,专门讲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他从唐代的景教一直讲到现代。那么,从唐代开始,公开的资料记载,635年阿罗本来到长安。至今已经接近1500年了。然而,在这近1500年的时间里,这些教会始终没有发展成像拜占庭帝国那样,政治与教会之间有非常紧密合作的模式。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不断有人被教会派遣去中国传教。这只能说明一点:上帝爱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事工也部分参与其中。虽然我们主要是从学术角度进行介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关于教会的历史,人们通常认为它始于宗教改革时期。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前发生了什么?似乎没有明确的概念。我认为这是不好的。你了解一个传统,必须先从它的历史去了解。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历史,你怎么能说你了解这个传统呢?它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这恰恰是我们光从东方来事工需要补充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在之前已经详细讲述了新教的历史,甚至可以进一步探讨天主教的历史。这当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西化过程。因此,在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期间,我们就有机会一并把这些内容纳入讨论。大家多多了解。但是我们的教会论始终是以欧美为中心的概念。但实际上,在早期教会,教会的中心并不是在欧美。它在哪里呢?它在现在的拜占庭帝国,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地区。比如中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叙利亚地区。
不久以后,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在圣司提反(Stoningof Stephen)被石头打死之后,受迫害被驱散了。基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玛特泰福音28:1》。他们遵从了这条诫命,在所到之处传播福音,起先向犹太人,不久之后也向外邦人。圣路加的《使徒行传》记载了宗徒们旅行的一些故事;教会的圣传统保存了其他的故事。在令人惊讶的短时间内,基督教的小团体在罗马帝国的主要中心,甚至在帝国疆界之外涌现出来。
首批基督教传教士(即指宗徒们)穿越的是由众多城市构成的帝国,特别是在东部地区。这决定了原始教会的管理结构。基本的单位是每个城市的基督徒团体,它由自己的主教管理:协助主教的是长老或神父和执事。周围的农村依赖城市的教会。这种模式,以及主教、神父和执事的三级圣职在一世纪末期已经在一些地方建立起来了。在安提阿主教圣伊格纳修(St.Ignatius)于107年将赴罗马殉道时所写的七封短信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点。圣伊格纳修着重强调主教和圣体血圣事这两件事;他认为,教会既是教阶性的又是圣事性的。他写道:" 每个教会由主教代表天主管理 “。” 在主教不在的情况下,没人能够管理任何教会事务……主教出现在哪里,信友们就在哪里,就像耶稣基督在哪里,大公教会就在哪里。 "
主教首要和独特的任务就是主持圣餐礼—『永生之药』。2
*2《致马尼西人书》(To the Magnesians),第4章,第1節;《致士每拿人書》(to the Smvrtuwuns),第 8 章,第1, 2 節;《致以弗所人書》(To the Ephesians) ’ 第20章,第2節。
阿甲按:人间真的有不朽药?
主教的主要工作是庆祝或举行圣餐礼。在圣伊格拉丢的观念中,这个圣餐礼被称为不朽良药或不朽药。如果当年秦始皇派徐福去寻找不死药的时候,他跑到了东方的拜占庭帝国。说不定能找到不死药。那么这个不死药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圣餐。在早期教会的传统中,就将圣餐称为不死药。为什么呢?在伊格拉丢的传统中,或者说早期教会的传统中,圣餐与普通的食物是不同的。我们有些人可能观念太先进了,就认为圣餐仅仅是上帝临在的一种象征,或者仅仅是上帝的临在。但早期的这个使徒教会其实并不是这样看待的。他们把主耶稣说的话当成字面意思。比如,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是字面的意思。它就是。那是我的宝血。那么它就是字面的意思。是的,是我的宝血。那么,在传统教会中,为什么这种观点占主流呢?因为早期教会就是这样做的。后来我们批评罗马天主教变质说。为什么罗马天主教会后来有变质说?就是说这个圣餐的饼和杯,就改变它的本质成了真的主耶稣的身体。但这种加入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论证方法其实僭越了上帝的奥秘。这点不为东正教会所认为。因此早期教会把这个圣餐称为“圣奥妙”或“圣奥秘”。它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在礼仪中虽然可以体验到它的意义,但其本质仍然是神秘的。祝圣的饼和杯,已经是主耶稣的身体而宝血了。但是它如何成为这样的,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圣奥秘。我们普通的食物吃到肚子里后,会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成为我们身体能量的一部分。然后有一部分变成我们的排泄物。任何地方的任何美食都是如此之过程。我最近翻译了艾弗伦的诗歌。他说我们吃进去的所有食物,最终都会变成我们的排泄物。你看排泄物,就是屎和尿。看起来多么肮脏,多么恶心;闻起来多么难闻。但是这样表达后,我们对这些食物的看法就是:它们只不过是普通的食物。但是我们。你说的圣餐不是这样子的。你所说的圣餐并不是我们把圣餐消化吸收,然后圣餐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是我们被这个圣餐消化吸收了,我们变成了这个圣餐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通过圣餐与主联合。就像头和身子一样,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这种联合是在领受圣餐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领受圣餐是真正且必要的。圣餐是真正的不死药、不朽药。如果当年秦始皇找到了基督教,那么他就应该成为基督徒,然后领受圣餐就好了。他就可以获得真正的不朽和永生。
阿甲按:科技不能让人不朽。也许有人问:你说的不朽,如果未来科技非常发达,医学足够好了,人类可以肉体保持不朽。那这是不朽吗?这当然不是不朽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永远活着,心中还非常肮脏,充满了邪念,你觉得这是一个人获得不朽的状态吗?如果秦始皇当年真的获得了一个让他肉体永远活着的不朽之身,那中国的历史将会是多么惨烈。这将是一部更加惨烈的历史。中国的这段历史会是怎样的呢?是吧。所以,比如说谈到不朽。有人会说:“AI是不朽的。”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复制它的语言模型。复制之后。字面上就是不朽的。但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不朽。我们目前没有看到AI具备与上帝交流的能力,也没有看到AI具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人格。所以这谈不上不朽。真正的不朽才是与那不朽者,战胜死亡者,主耶稣联合,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今生,因为今生的一切都会朽坏。即使你是AI,也需要更换承载它的硬件。这个硬件无论是铁做的、金做的还是银做的。它也不是不朽的。道家说与天地同寿,但是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他说:“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他还要更新天地,因为在这个天地间的一切全部都是会朽坏的。所以,我觉得圣餐就像伊格拉丘和使徒教父所说的那样,是真正的不朽。因此,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去教会领受圣餐。
今天的人们倾向于认为『教会』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其中的每个团体构成更大和更包容的整体的一部分。圣伊格纳修却不这样看待教会。对于他来说,地方团体就是『教会』。他认为教会是一个圣体血圣事的团体,只有当它举行『主的晚餐』(Lord’s Supper),在圣事中接受主的真实的圣体和圣血时,才能实现『教会』的真实性质。但是圣体血圣事只能在每个围绕者主教而聚集起来的特殊团体中举行;在每个地方的圣餐礼仪活动中临在的是【整个】基督,而不是仅仅是祂的一部分。因此在主日举行圣餐礼的每个地方团体都是完整的『教会』。
圣伊格纳修的教导在正教传统中具有永久的地位。正教仍然把教会视为一个圣体血礼的团体,虽然它的外部组织是必须的,但却次于它内部的圣事活动之后;正教会仍然强调地方团体在教会结构中的头等重要性。对于那些参加正教主教礼仪(Orthodox Pontifical Liturgy)3的人来说,当主教在礼仪开始时站在圣堂中央,被他的信众围绕时,安提阿的圣伊格纳修的"主教在地方团体中作为统一体中心"的思想,就会极其鲜明生动地表露出来。
*3 正教徒一般使用礼仪(the liturgy)这个术语指代圣餐(holy communion)祝谢餐(the eucharist)或弥撒礼拜。
但是除了地方团体之外,还有更大的教会统一体。另一位殉道的主教,迦太基的圣西普里安(St.Cyprian of Carthage 死于258年)在其著作中发展了这「教会论」的第二方面。圣西普里安认为所有主教分有同一个主教圣职,尽管分有方式是每位主教拥有的不是其中一部分而是其整体。他写道:“主教职是一个整体,每位主教都完全拥有它。因此教会是一个整体,虽然它深入而广泛地传播,随着’繁殖力’的增长,大量的教会出现了。“4
『教堂』(Church)有许多,但是『教会』(Church)只有一个;『主教』(Eposcopi)有许多,但是『主教圣职』(Episcopate)只有一个。
*4《论教会的统一》第五章
在教会的头三个世纪中,许多人像圣伊格纳修和西普里安那样作为殉道者结束了生命。事实上,迫害的性质常常是地方性的,通常限于一段时期。虽然在很长的时间内,罗马掌权者在很大程度上宽容了基督教,但是迫害和威胁始终存在,基督徒明白这个威胁任何时候都能成为现实。
殉道思想在早期基督徒的精神视域中占据中心地位。他们认为他们的教会建立在流血之上——不仅有基督的宝血,还有「其他基督」—殉道者的血。在后来的世纪中,当教会成为『国教』,不再遭受迫害时,殉道的思想并没有消失,但是却采取了其他的形式:例如,修道生活常常被希腊作家认为等同于殉道。同样的进路也出现在西方教会,例如,一份凯尔特文本——七世纪的一篇爱尔兰讲道文——将禁欲生活比喻作殉道者之路:
" 三种殉道被认为是人的十字架:「白色殉道」、「绿色殉道」、「红色殉道」。白色殉道的意思是人为了天主而舍弃他热爱的一切……绿色殉道是人通过禁食和劳作,使自己从自己的邪恶欲望中解脱出来,或在悔改和忏悔中受苦。红色的殉道意思是为了基督经受十字架或者死亡 “5
*5《爱尔兰修道主义》.J.Ryan
在正教的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红色殉道」的景象已经颇为遥远,占主导地位的是「绿色」和「白色」形式的殉道。但是正教徒和其他非正统的基督徒有时,尤其是在本世纪,再次被号召经历流血的「红色殉道」。
阿甲按:论血色殉道士与白色殉道士
说实话,如果按照维尔主教的说法,在苏共时期的苏联,仅仅30年的时间内,对基督教的迫害已经超过了以前罗马帝国在300年期间。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么可以说,现代基督教所面临的逼迫,并不比早期教会轻松。有一段时间,罗马对基督教采取了相当大的容忍态度。然而,对他逼迫的威胁始终存在。基督徒知道,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面临迫害。这种威胁可能变成现实。那么殉道者在早期基督徒中占据着非常中心的地位。早期的基督徒认为他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这些殉道者的鲜血之上的,不仅仅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还包括其他殉道士的宝血。因此,有很多殉道士,他们在罗马帝国时期宣布自己是基督徒。有些人来不及受洗就直接殉道了。很多基督徒认为他们是为主做见证的英雄,就把他们的遗骸收集起来。收集完之后,就在他这个尸骸之上建立一所教会。那么殉道者们还没来得及受洗,能得救吗?早期教父们就解释:殉道者为什么没有受洗就已经得救了呢?是因为殉道者是以自己的鲜血为自己施洗了。因此,这被称为“血洗”。他们用鲜血为自己施行了洗礼,见证主基督的信仰。后来,当基督教教会建立不再受到逼迫,基督徒们没有机会殉道了,但其精神并没有消失,而是采取了其他的形式,即修道主义运动。从此,为主受独身的修士们被称为白色殉道士。
正如圣西普里安强调的,分有一个主教职的主教们应该在会议中会面,以讨论他们共同的问题,这是自然的。正教一直认为会议在教会生活中极具重要性。它相信会议是被天主选中用来指导祂的子民的主要机构,它认为『大公教会』本质上是一个「会议的」(conciliar)教会。(事实上在俄罗斯,同样的形容词’soborny’具有「大公的」和「会议的」双重含义,而相应的名词’sobor’表示「教会」和「会议」两个意思。)
教会里既没有独裁也没有个人主义,有的是和谐与一致;其成员保持自由但却不是孤立的,因为他们在爱、信仰和圣事的共契中联合起来。在会议中,人们看到这种和谐与自由一致的理念实际发挥出作用。在真正的会议中,没有一个成员武断地将他的意志加诸于他人,每个人都与他人协商,他们所有人以这种方式自由地达成「共同思想」。会议生动地体现了教会基本性质。
《使徒行传》第15章描述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会议。宗徒们参加了会议,会议在耶路撒冷举行,确定皈依的外邦人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服从摩西的律法。当宗徒们最终达成意见时,使用了在别处会显得专横的语言:” 因为圣神和我们定意…… “《使徒行传15:28》。
后来的会议也以同样的信心冒险说话。一个孤立的个人如果要说"因为圣神和我定意”,会很犹豫不决;但是当教会成员在会议中聚集时,能够一起要求一个权威,这个权威不为任何人所具有。
曾经聚集了全部教会领袖的耶路撒冷会议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聚会,因为在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以前,没有会议能够与之媲美。但是到圣西普里安的时代,举行地方会议已经变得普遍,出席地方会议的是罗马帝国内特定国家行省所有主教。这种类型的地方会议通常在行省首都举行,由有着都主教头衔的首都主教支持。
公元三世纪中,会议扩大了规模,开始吸纳不是来自一个而是来自几个国家行省的主教。这些较大型的集会倾向于在帝国的主要城市,例如,亚历山大或者安提阿召开,致使某些大城市的主教的重要性开始高于行省的都主教。但是眼下并没有确定这些大主教教区的确切地位。在公元三世纪时,会议的连续扩展也没有实现其逻辑上的结论:那时只有程度上或大或小的地方会议(除了宗徒会议),而没有由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教们组成的「全体」会议,要求以整个教会的名义发言。
阿甲按:论教会地方会议与早期国家行政疆域的关系
直到325年的尼西亚会议才产生一个与耶路撒冷会议几乎同等的教会会议。这并不是说,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教会没有产生任何会议。在居普林安的时代就已经有定期举办的地方会议了。参会人员是罗马的一个省份的城市主教们。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例如,如果是在中国早期教会的情况下,比如湖南省可能有多个市,如长沙市和衡阳市。每个城市的主教们会定期前往长沙市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可能持续三天到一周左右,旨在探讨湖南省地区基督教信众的教务问题。大家将发表意见,并可能产生一些会议文献,然后发布通告。然后把这个通告传播到湖南省内所有的乡镇教堂里面,让这些神父们都了解。这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像那种大公性的活动,即整个教会都参与的,那确实是只有在尼西亚会议的时候才开始。在罗马帝国的主教通常被邀请参加地方会议,这些会议一般在各省省会举行,由在这个省省会的主教主持召开。例如,我们以湖南省为例。如果他是长沙市的主教,那么他自然就是长沙市的都主教,即metropolitan。大家不要以为metropolitan仅仅是罗马帝国的个别现象。其实,在同时代,几乎在四世纪的时候,波斯帝国也是这样的。在叙利亚教会中,他们按照波斯帝国的省份划分。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2个metropolitan。那么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其实就是他们波斯帝国省的这个省会。其实同样一种模式。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哇,早期教会的治理模式为什么这样?但其实不奇怪。当时他自然就发展起来了。罗马帝国就是这样,波斯帝国也是如此。罗马帝国的省会也是这样。那么你问我,当时的亚美尼亚教会是否也如此?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的。
312年出现了一个完全改变教会外部状况的事件。当君士坦丁大帝骑马带领其军队跨越法兰西时,他向天空望去,看见太阳前面有一个发光的十字架。十字架上有「见迹得胜」的字样。这幅景象导致的结果是,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那天在法兰西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带来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主要阶段的终结,造就了拜占庭的基督教帝国。